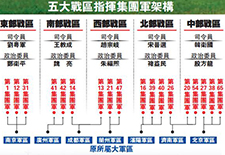魔焰炽盛,亦可全真:林谷芳与知识分子论禅

林谷芳(图片来源:资料图)
“禅者”林谷芳说禅的特点之一是“不鸡汤”,他会带着“问题意识”,谈微博、谈死刑废除、谈知识分子。
“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是拉车与刹车。公共知识分子扮演拉车的角色,让这个社会更合理。但公共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应该是一直互补、一直调整,也就是动态而有机的,否则副作用就出来了。”
63岁的林谷芳站在冬天北京的街头,只穿一身棉布裤褂。据说他一年四季都这样穿衣。再冷,也不过是脖子上搭一条白色围巾。这甚至成为他佛学修为高度的一项佐证。在台湾,林谷芳有很多身份:民族音乐学者,文化评论家,台湾第一本文化白皮书的撰写者,“国家文艺奖”评委,台湾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。现在,他更愿意只剩下“禅者”这一个身份。
“禅者的慈悲是告诉你生命可以这样做减法、这样不执著,人人都可以做到。”林谷芳说,最直观的“减法”,是一个人的外形、装束。
2013年,林谷芳与北京晚报记者孙小宁的问答录《观照——一个知识分子的禅问》出版。两人的问答历时3年,孙小宁以自己的各种困惑叩问林谷芳:微博、乔布斯;该不该废除死刑;为什么我们更容易和弱者共鸣;当下知识分子的思维是否过度西方化……
他们上一本关于禅的对话录叫《如是生活如是禅》。“所谓‘安顿心灵’的书这些年出了不少,和禅有关的不少被划到这一块。”作家出版社编辑李宏伟说,“如果说把禅或者佛视作传统文化,可以说,‘鸡汤化’是这几年传统文化与大众阅读的有效衔接。”
李宏伟这次出“观照”,恰恰因为它“不鸡汤”,其“问题意识”及“看问题的角度值得认真对待”。
什么时代,会满街都是搓佛珠的人?
记者:大陆很多人会搓佛珠,把“禅”字印在杯子、扇子、T恤,谈禅的书成为流行出版物。你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吗?你怎么看?
林谷芳:我们以为我们哪一天物质富足了,就找到生命的安顿了,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。失望之余,就有很多“解药”出现,比如传统、宗教,很多人会向此处去求。但多数是“心外求法”——就像一味追逐名车、追逐财富、追逐地位一样。很多寺院的和尚动不动在比念珠有多贵,自己异化,也让众生起颠倒。另一方面,人家都来找“禅”,也有禅自己的原因。
第一,禅不立文字,有时候“随你讲”,这就提供了鱼龙混杂、鱼目混珠的空间;第二,禅比较嵌入生活,不是说你非得读完“三藏十二部”才能理解。这些都是大家想运用禅,随便附一句禅语做logo的原因。其实都是“外相”。“禅”这字在传统,如果没有特别地去标注,讲的就是祖师禅。祖师禅对应于如来禅,也就是经达摩、六祖慧能所开启的一脉,它有它特殊的观照,特殊的修行。而不是说,打坐就是禅,或者你啜饮一杯咖啡就是禅,生活恬恬淡淡就是禅……
记者:禅的泛化和时尚化,在台湾明显吗?
林谷芳:也有,但没那么严重。群体认同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。有了网络之后,这个时代就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谈“流行”的时代,最易出现“群体性感染”。“革命”、黄老、儒释道都可能成为流行资源。但越是一窝蜂,真正的“返观”越不容易实现。而“返观”却是宗教和理性社会所必需的。
记者:从林清玄、胡茵梦到现在,禅在台湾热了好多年,背后的社会心理是什么?
林谷芳:林清玄、胡茵梦谈的也不是祖师禅。禅被概泛而论,是因台湾1960年代来的发展跟佛法的复兴是密不可分的。大陆谈台湾很多社会现象时,没有把握住这一条,就一直没能找到关键点。譬如说,台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志工(志愿工作者)?台湾志工绝大多都是来自佛教界。至于说禅在台湾长久兴盛,第一,大概因为它是最具中国特征的佛教。第二个跟1950年代、1960年代的时尚风潮也有很大关系。譬如我在台大读书的时候(1960年代),谈文史哲,如果三样东西你不懂,你就落伍了:禅、存在主义、心理分析。
记者:你说的近四十年佛法在台湾的复兴,是知识分子推动的,还是佛教界推动的?
林谷芳:最重要是佛教界。知识分子对禅感兴趣是因为1960年代大家都追逐西方,而西方也在谈禅,这样折射回来。禅在台湾两次“时尚化”都跟知识分子有关系,一次就是刚才提到的1960年代,谈禅,谈存在,是知识分子的时尚。第二次是在1980年代,知识分子开始谈雅皮了。雅皮如果你没有一种生活品位,没有一点哲学背景,你也不要混了,你那雅皮就只是一个恋物狂而已。
但佛教界不一样。当年“国府”撤退的时候,大多数的宗教界人士,不只儒释道三家,还有本土的天德教、天帝教、理教……全部都到台湾去了。那些修行人在一穷二白的1950年代,而不是经济起飞之后的1970年代,就开始大量印制经书了。他们认为如果不印,道会断绝,传承会断。像全真教,现代社会一万个人可能也找不到一个人去修它,但它照样也把经书都印了。这样的社会现象,《天下》、《远见》一类的主流杂志不会关注,主流台湾社会还是以知识分子为主,以世间法为主。
事实上,台湾社会有两个文化现象非常特殊:一个是1950年代宗教界默默印制经书,一个是1982年、1983年之后,台湾的天主教跟基督教人口没有增长过。这其实有非常大的文化意义:因为在西方500年来的殖民史里面,洋教在受西方影响下的社会都是优势宗教,它也许不占人口的最多数,却是代表成长快或者位阶被看得比较高的宗教。
记者:一般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会出现禅大规模进入社会生活——说粗鲁一点:什么时代,会满街都是搓佛珠的人?
林谷芳:禅只是佛教里的一宗。而且这一宗号称“教外别传”,跟一般佛教的态度不太一样。“教下”的宗派都讲究佛相庄严,可是“教外别传”的禅画却有很多幽默、滑稽、自我颠覆、自我揶揄的成分。过去禅堂都不立佛像,它当然更不会依赖于一个念珠。所以你说的“佛珠现象”只是一种宗教现象,就像大陆现在有那么多基督徒一样。
一般的规律,“乱世”容易产生宗教现象。但也不尽然,比如说有些民族,像印度本来就是个宗教民族,它无时无刻不观照着宗教问题。中国文化比较是一种人间性的文化,也因此,它的宗教现象特别凸显的时候,大多在一个浮动的时代。但禅不一定,禅最盛的时候在唐、五代。唐代是盛世,很多人有勇气直接面对自己根柢的生命问题,想要去做一个终极的解决。
过去禅家讲,习禅是“剑刃上行、冰凌上走,稍一放浪,就丧身失命”。我写《禅两刃相交》时,在序言里特别提到:不能以禅为趣、以禅为美、以禅为学。虽然禅可以为学,可以有趣,禅绝对跟美学有关系,但不能尽在此转。作为一个禅者,我特别强调禅的“不共”。
记者:“不共”怎么讲?
林谷芳:不共是它与其他宗教、修行,乃至佛教诸宗的不同,禅以最严厉的态度挑战生命最根柢的困境──生死,希望在此超越、解脱,它认为死生缠缚、烦恼颠倒都来自生命对“自我”、对“法”的执著,谈自我的超越要“超凡入圣”,谈“法”的超越就须连圣都破掉,要“超圣回凡”,只有“凡圣双泯”才能自在,所以禅举“只破不立”,这与其他宗教根本而庄严的“立”不同,禅家的活泼其实由此而来。
为什么社会良心变成社会负担
记者:你在“观照”的前言里有一段话:“殊胜的道德固可以理教杀人,傲人的学问更常让知识分子自设牢笼,也因此谈生命的安顿,知识分子还常不及黎民,不能自我安顿的生命却夸夸其言于天下大事,虽说言不必因人而废,但其间的吊诡、异化,的确值得我们反思。”这些意见针对什么现象而发?
林谷芳: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有很大的关怀,好像我们要负担起天下大事,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“大德不逾闲,小德出入可也”。但其实,这里面有很大的危机。因为有一天那个“小德”也会变“大德”。所以禅回答所有的问题都有针对性,它不会告诉你一个“普适”的原则。
以台湾为例,台湾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末到2000年是社会的重要资产,在2000年以后许多人却让社会头痛得不得了。大概有几个原因:知识分子,尤其“公知”,为了推行他的理念,总孜孜矻矻、摩顶放踵,不计其他。而且越早“出道”,后面的生命里越没有学习,没有学习再加上孜孜矻矻,就容易把自己的观念极端化。
有一次我的家乡新竹海埔新生地,要做一个国民住宅。那当然不好,破坏生态,因为很多水鸟栖息在那里,国民住宅还可以到别的地方盖。一群社运的人士一起去反对。我有一个朋友一进去,就走出来,他说会开不下去。因为第一个起来讲话的人是新竹鸟会的秘书长,他义正词严地问大家:你们说是鸟重要还是人重要?问得人哑口无言。这就是知识分子常犯的错误——因为我们太关心一件事情,太以为一件事情是对的,再加上又把一生的精力花在上面,所以就把单一的概念极端化。台湾的教改、台湾的环保、台湾的政治运动都有这个问题。
我相信,在这里大多数人是有他的善意,乃至社会良心的,但后来为什么会变成社会的负担呢?从禅讲,过了那个临界点,你对待问题的方式就失效了,这个时候需要调整。此外,当我们一直想改变社会,这个社会不随我们的意念而改变,人就容易焦虑,而时间又一直在流逝,过了五六十岁发现这个社会好像没照我的意思走,人就焦急,就开始愤世嫉俗。所以许多过去很从容的人最后都变成“老愤青”,也接纳不了别人的意见。可大家也拿他们没有办法。因为他们拥有话语权。他们态度是坚决而且是神圣的,没有沟通的余地。
我不见得表现得比你们好
记者:你1968年放弃在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的学习,去参禅访道,1988年又回来作为一个评论者参与台湾的文化建设;跟着2000年又放下这个身份,回到禅修;2011年“入世”又出来做台北书院的山长……每次出世入世都是什么机缘?
林谷芳:我上大学的时候,大陆搞“文革”,对应于此台湾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,官方开始关注传统。在此之前,台湾非常新潮。因为1949年过去的“国府”精英,多数都有“五四”的经验,而“五四”就是否定传统的。到了1950、1960年代,台湾有“留学热”,那时候的流行口号是“来来来,来台大;去去去,去美国”。可你到了美国,人家却问你:你的东西是什么?像林怀民这些人都是当时被问才回头的。
我这样留在台湾的,在1960年代末一方面感觉到中国文化热,另一方面又觉得大家谈“文化”常失于两极——要么从西方的角度看,要么从国学的角度看,都难免有情绪性。不如去找一个以文化这个概念为核心的学科去学习吧,所以我进了台大人类学系。但学了一两年,感觉这学问与死生终究有隔,靠学问这一套来解决死生的事情是不可能的,总之,它与我根本的生命情性不符。所以在大二的时候就把它(人类学)放下了,去各个寺庙、道场参禅、访道。
记者:为什么你1988年又出来评议文化?消失了20年再出来,你的话语权从哪里来?
林谷芳:跟我做中国学问有关系。那时候“独派”已经起来了。1990年代初,有一次我从青海回来,有人问,你为什么常跑大陆?我回答了一句话,是我心底的话:我去“印证生命所学的真实与虚妄”。因为我年轻时读的是中国书。禅者对生命应该有一个真实的态度,如果你有机会去参究、勘验,你为什么不去呢?
我往来于两岸,是在印证我的学问。开始出来做事,那是要一条血路杀出来的。以高信疆为首的文化人如林怀民、蒋勋、龙应台等,他们都在1970年代或1980年代初就掌握话语权,彼此相熟,互相呼应。我不是。我没有别的法门,就是一直写,一直参与,在那个年代,可以说“无役不与”。但最初也都只能发表在不太显眼的地方。1996年,我出来已经8年了,在音乐界也算小有话语权。《谛观有情》出来,痖弦说:林先生你出这本书,我《联合报》副刊登你的序言好了。结果我把序言寄给他。70天之后,序言才出来,新任的主编没经我同意把前面一两段、后面一两段都去掉了——这在台湾是其他文化人不可能有的“待遇”。
到2000年,我觉得我可以退出文化评论这个江湖了。台湾有一群文化精英,三十岁就名闻台湾,到六十几岁还在第一线,这不是正常的现象。我不是,该走就走,该退就退。
记者:台湾第一本文化政策的白皮书,是你起草的,当时你要处理什么问题?你提出了怎样的方案?
林谷芳:其实那是台北市文化政策白皮书,是台湾的第一本。当时阿扁当市长。我跟他的文化立场、政治立场都不一样。他们找我纯粹是个意外。他们第一个去找的是南方朔,没答应;第二找杨照,也没答应;第三个来找我。我刚好在此有意见,那我就写:台湾只有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观其远,成其大。
记者:估计阿扁不喜欢这种说法。
林谷芳:是。但是当时邀稿的罗文嘉(台湾政治人物)不错,他的意思是:既然委托老师写,那当然要尊重老师的意思。他不容易,当时的政治氛围我要那样写也不容易。1990年代中期,亨廷顿提出文化冲突的理论,我在台湾文化界就一直强调“文化板块”之说,强调:未来的文化没有“世界”这两个字。未来的文化是文化板块,中国板块、印度板块、伊斯兰板块、欧美板块……没有办法在板块发声就没有办法在世界发声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劝云门到大陆来:毕竟,即便《纽约时报》说你代表东方,北京也会抗议,说没经过这里你怎能说你代表东方。
记者:你说过大陆是一个参不完的大公案,最近这个大公案你参到什么地步了?
林谷芳:这些年大陆急遽地变动。前期我比较观照中国文化在这变动下如何因应,而现在关心的则是,在如此急遽的变动中,人如何安顿自己。这是一道生命根柢的大公案。台湾常有人跟我说:林老师,我们钦佩你,你以布衣傲公卿。我说在禅者,这很简单:干我何事?他有钱有权,与我何干?但我常常跟大陆的朋友讲:放在你们的环境,我不见得表现得比你们好。修行的人,最该懂得设身处地,这是我很真诚的一句话。但尽管如此,正所谓“魔焰炽盛,亦可全真”,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观照,让自己活得更纯粹一些。
- 佟大为:一个人有信仰绝对是一件幸福的事情2016-02-24
- 长期禅修对乔布斯的影响:灵感都来自佛法2016-02-17
- 蔡志忠:生命的实相在于当下 学习其实是很简单的事2016-02-17
- 熊十力:“举头天外望,无我这般人”2016-02-16
- 钱穆:国学大师的静气与豪情2016-02-02